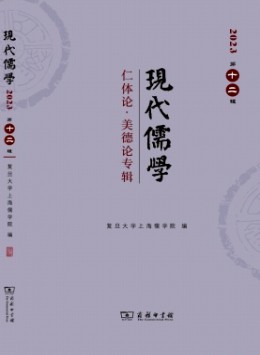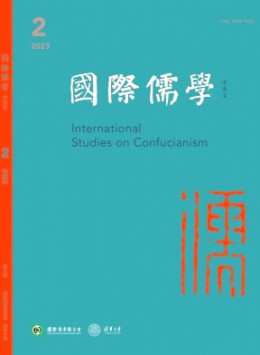儒家性善論的兩種型態與演進邏輯——兼論其義理困境及更化路向
作者:鄒曉東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; 山東濟南250100
摘要:儒學史上存在兩種性善論:界定本體的性善論與不界定本體的性善論。回歸最基本的生存問題,歷史地檢討這兩種性善論的學理得失,可以有效地促成儒學義理的更新轉化。作為最原始的性善論形態,“不界定本體的性善論”始于《中庸》對無所不在的“真知”問題的著重揭示與專門回應,這是一種融貫一致且以“率性”意識為中心的性善論。其短板在于:無法有效容納傳統德目與施教權威,其服膺者在“自作主宰”精神的鼓蕩下,往往難以組成和諧有序之社會。“界定本體的性善論”則試圖以傳統德目規定“善性本體”,這固然容納了社會智識傳統與政教權威,但卻因為推崇、仰仗既定的教義與外在的治教,而架空或放逐了內在善性即時指引的活潑功能,故實質性地落入“重教—外鑠—性惡”的荀學思路。論其實,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性善論。在“不界定本體的性善論”基礎上,自覺引入或充分強調“率性的處境”與“共識的更新”這兩個維度:將“傳統教義”“施教權威”以及“他人異見”統統歸入“率性的處境”范疇,并力求通過一輪又一輪的“在新處境下的率性體認”,不斷就公共事務達成“新的共識”——這種充滿張力的動態機制,應是傳統儒家性善論更化升級的新路向。
注:因版權方要求,不能公開全文,如需全文,請咨詢雜志社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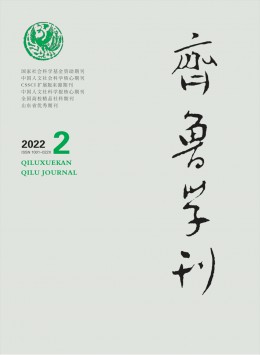
齊魯學刊雜志
齊魯學刊雜志, 雙月刊,本刊重視學術導向,堅持科學性、學術性、先進性、創新性,刊載內容涉及的欄目:孔子·儒家·齊魯文化研究等。于1974年經新聞總署批準的正規刊物。
- CSSCI南大期刊
- 北大期刊
- 1-3個月審核